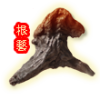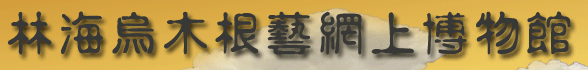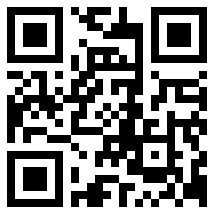浅述乌木文化的特征
(2012-02-09 15:35:53)标签:
文化 |
分类: 乌木 |
浅述乌木文化的特征
乌木文化,一则谓,以乌木神话时代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为本源,贯通华夏民族史上,通过乌木物态模式现象,得以反映的历史人文环境,以及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环境。二则谓,以乌木神话时代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,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的乌木思想,主导中华文化的进程,成为中华历史社会大众共存万法实践之宗源。
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人文环境,主要是第四纪晚冰期消融这一特大的主题事件,注入巴蜀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,形成以洪流为历史破坏性指标的生态进程中,巴蜀文化的演进无法避齐,“洪灾”这一生态背景的约束,和“天府之国”优越生态环境的吸引,产生认识自然,利用自然的因势利导思想,构成巴蜀先民以成都平原作为天堂的,特有的生态人文气质。乌木物质作为巴蜀生态背景的产物,其形成实况,对巴蜀先民当时的人文思考,和作为历史灾难记忆的传承,在更早期的乌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,共同合成的人文乌木,又构成巴蜀生态文化中特有的乌木人文气质。乌木人文成为生态人文的具体表现,以乌木物质和乌木模式作载体,代代传颂至今,这就是川人俗称乌木的来源。由此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人文环境,是乌木文化不可分割的版块。
乌木模式的存在状态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用了“乌”和“木”两种基本的物态技术为特征,体现乌木思想发挥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客观现象。
为了明确乌木模式和乌木思想,所处历史环境阶段中的特征,对其历史时期进行划分,夏朝之前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;夏朝至汉朝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;汉朝至鸦片战争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;鸦片战争至1980年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;1980年至今,谓乌木文化现实期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,主要以乌木神话为特征,乌木神话分别以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等乌文化和木(树)文化为代表,构成华夏民族创世文明的乌木神话时代。
史载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主生众鸟,亦为驮载太阳的神鸟,从黑暗中给大地带来光明;建木,立于天地之中,为众神上下天地的天梯;扶木、若木,一东一西,为乌之栖所。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等神话,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史前史,作为旧世界文化的终结,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,开启了创造新世界文明时代的历程。
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为标志的乌文化,以“三”代称“天、地、人”的概念;以“乌”代称“黑暗、光明和自由”的概念,在史前史,天、地、人共存的环境中,效法太阳(光明)、鸟(自由)、黑暗(阻碍大众获取光明和自由的一切天灾人祸)等自然物哲理之间的形象辩证,经过漫长时期的实践,总结出大众活动的宗旨在于“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。
“建木、扶木、若木”为标志的木文化,在对树崇拜的基础上,仍然凭借自然哲理的形象辩证,以木表达大众对光明的需要,就象树对太阳的需要一样,唯有光明的生活,大众才能象树一样自由成长。以扶木、若木表达大众生存的地理环境,在以建木为中心,从西到东的地域。以建木表达大众需要建设,保护大众生存及其环境的领导中心,经过长期的实践过程,总结出大众活动的根本思想在于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”。
以东扶木,西若木,为乌之栖所,表达乌文化和木文化的互动结果,产生了乌木文化;同时表达了建木所在地,是乌木文化的发展中心,一个实际存在的乌木王国诞生了。乌木文化以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,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的乌木思想,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先河,标志着大众历史从人文启蒙主义的世界,走进了人文生态主义的世界。
大禹建立夏王朝的成功,可谓乌木文化在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开篇巨作。尧、舜、禹所处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天灾是洪水,最具代表性的人祸是十日争霸,即流传于后世的十日神话。十日神话内容甚多,如史书载:尧射十日、羿射九日、帝俊生十日、十日浴汤谷、十日栖息于扶桑与若木、十日齐现天空等等。十日神话之日,义同三足乌,为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领袖;十日之十,为多数。十日,为产生很多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领袖,即为乌木文化的社会具体现象。因十日出现天空,万物焦枯,产生“尧射十日”(羿射九日乃夏王朝建立之后事),即“十日争霸”的社会尖锐矛盾。“尧之时,十日出,万物焦枯,尧上射十日,九日去,一日常出”。尧之时,十日争霸的社会矛盾得到解决,大众奉行乌木文化的思想得到弘扬,显示乌木文化发挥了强大的领袖力量。
今四川地区发掘规模的乌木实物,佐证了史书记载尧、舜、禹时代天灾洪水的真实性。在禹的领导下,天灾洪水及其伴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,随之而新生的夏王朝,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,结束了华夏民族一盘散沙的历史。在尧、舜、推崇乌木文化日渐光明的基础上,大禹王集团以民为本,把“乌木王国”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的理想变成了现实,以国家文明里程牌的创举,开发出一片乌木文化的新天地。
把一个大众生存的恶劣环境,变成了一个大众共存的良好环境,揭示出大禹王集团对待“天灾人祸”的生存环境,已经拥有了系统的环保思想和措施,其目的实现了乌木思想的要求,说明大禹王集团环保思想,是乌木思想之环保哲理内涵的具体表现。大禹王堪为中国文明史上的“环保大英雄”。
尧、舜、禹是中国历史上,乌木思想产生的社会主流文化现象。大禹王的成功,是乌木思想的成功,标志着一个具有社会管理能力,爱护大众共存环境的乌木文化集团已经诞生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主要以乌木历史事件为特征。乌木历史事件主要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,和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船棺群为代表的船棺文化,他们以乌木模式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,这些事件具有浓厚神奇的乌木文化氛围。
青铜神树(同时出生的还有几棵残断的青铜神树)诞生在商殷时期的武丁时代,它承载了两组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鸟、三枝、三层、火轮、树”等构件的乌木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悬龙、刀、剑”为构件的龙文化信息,构件各执于树干之周围,组合成视觉冲击强烈,文化信息深厚博大,情志色彩沉稳忧患的青铜作品。无疑,青铜神树信息记载了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的历史意义,标志着乌木文化的传承持续到了青铜神树诞生的时代。
“龙”是以黄帝为系统的北方文化集团的图腾,“刀、剑”是战争的象征。武丁时代,武丁发动了同历史相比,规模巨大的战争,“悬龙生刀剑”的信息;即是对武丁时代战争的真实记录。青铜神树两组信息都有独立的历史背景,表达了乌木文化集团与龙文化集团之间,治理社会不同的政治主张。乌木文化集团对龙文化集团采用战争手段进行了坚决的反对。由此,说明乌木思想在夏朝和商朝武丁之间的历史时期,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行为主导作用。青铜神树作为武丁时期乌木文化艺术的时代杰作,亦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丰碑,透示出乌木思想在当时社会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地位。
从商朝到西周,乌木神话还在继续,玄鸟生商,巨鸟救后稷,意在传说商朝和西周都是三白乌的后代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夏、商、西周的兴盛衰亡都跟“大众共存、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乌木思想存在直接关系,王者爱民则国兴;王者欺民,则国衰;王者弃民,则国亡。
船棺文化出现在春秋时代初期,至汉朝初期,共五百余年的时间,主要活动范围在巴蜀地区,是乌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代表。船棺文化对中国后世殡葬文化的影响巨大,黑(乌)色船型棺具,是船棺形式的发展,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至今,即为一大例证。船棺文化的本质是:春秋战国时代,出现诸侯争霸,列国争雄,诸子百家文化茂生的悲世局面。中国大地悲患四起,乌木文化集团的理想和抱负失去了生存环境,那些热爱大众共存,愤恨时代凄凉的子民们,在极端痛苦的命运挣扎中,孕育了“生不得志,死而宿愿”的信仰,创造了以乌木神话时代为精神导师,以先民的遗志为召唤,以行走天下的船木为葬棺,安置灵魂的殡葬文化,成为世界殡葬史上的奇观。船棺文化体现了乌木思想,在历史环境大变动的悲惨状态下,对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所起到的主导作用,有力地证实了乌木文化群体信仰,在群体灵魂祭拜大众光明文化的山峰上,为中华民族树造了一座乌木灵魂之塔。
春秋战国时代,是中国历史走到“大众共存”最为艰难的时期,它严重违背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与“乌木王国”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,没有夏、商、西周以民为德,中央集权的光明大器。以东周的建立为转折点,乌木思想急剧衰退,一直到汉朝,诸子百家文化无首——这是一个人祸黑暗压倒光明的时代,船棺文化尤如乌木的灵魂,在被魔鬼吞食的搏斗中留下的一点灵光,却明亮的可以穿透历史,照耀未来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主要以乌木文化艺术为特征。乌木文化艺术主要以成都出土的汉代文物摇钱树,和金乌画像砖为代表,他们散发的洋洋喜气,尽致地表达了盛世汉朝的辉煌成就,摇钱树运用树模式的艺术形象,同历史上青铜神树、船棺文化托载各个时代的重要社会事件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;翔天飞舞的金乌画像砖,同十日神话、玄鸟生商、巨鸟救后稷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三白乌、三足乌。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,他们承担了同历史环境相应的使命,成就了不同环境的历史,共同选择的精神领袖。汉朝,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管理的太平盛世,代替了一个结束诸侯争霸的混战历史,统一全国后,又迅速瓦解的秦朝,其乌木文化艺术的喜庆同船棺文化的悲沉相比,证实了汉朝在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道德、经济、艺术、民俗等多方面,主张“天下太平,百姓安宁”的大众共存世界,仍然应用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并同先道后儒的文化模式一起,为汉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。退出历史舞台五百多年的乌木思想在汉朝得以复兴。
中国二千多年来,道儒佛为主流的文化格局,起始于汉朝。道儒佛文化都在宇宙、自然万物、国家、社会、人性、哲学、医学等多方面,各自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系统成就,却都运行在乌木思想的宏观世界里,以各自不同的本源主张学说,去实践乌木思想的旨趣,成为乌木思想宏观机理的受益者。
道文化以大道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自然法则,修无为,以道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儒文化以天、地、人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和谐辩证法则,修有为,以儒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佛文化以人心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清净轮回法则,修无为,以佛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乌木文化的出现,以创世文明的形态早于道、儒文化四千年以上的时间,都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,都对中国历史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主导性。汉朝之前的道儒文化雏形已经产生,以禹、汤、文武、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“小康社会”,即是儒文化的雏形社会原态,又是道家文化的温床,同是乌木文化成功的典范。春秋时代集大成的道、儒文化领袖人物老子和孔子,为了解决现实矛盾,拯救天下大众的痛苦,鉴古证今
汉朝时期,以道、儒、佛文化作为乌木文化的新面貌,向纵深发展至今,标志着中华文化经历了,从人文启蒙主义到人文生态主义,再到人文形学主义的历史进程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主要以乌木民俗文化为特征。乌木民俗文化主要以四川民间供奉乌木神灵,乌木神话故事流传,乌木饰品、乌木棺材、乌木家俱、乌木文房诸宝等为代表,它们保存了乌木神话时代的神秘性,并增加了娱乐性、收藏性、实用性功能,与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,盛兴之后的乌木民俗文化一样,同外界的交流范围大大缩小,偶有民间活动。乌木文化模式在社会政治、教育、文化艺术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复存在,表现为民间的散传形式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,作为中国与世界矛盾的分界点,中国文化从此与世界文化发生激烈碰撞,发展到全国性地多次卷入到矛盾的最高形式,第一次世界大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,在如此变幻莫测的时段里,中国道儒、佛等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。与此同时,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,战胜了外敌强权的侵略,和统一国内矛盾建立了新中国。马克思主义,毛泽东思想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则,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世界,同乌木思想是一致的,不同的是在具体的环境中采用了具体的方法。新中国的建立,完全可以看作是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,化解了更高级的社会矛盾,其哲理的宏观作用,是无以能比的。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,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代表的严重错误,又一次破坏了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”的社会行为准则,造成国家和大众的艰难局面,短短的140年的时间,中国社会遭受了巨大的人祸灾难,乌木文化没有中断,被天府之国传承下来,以乌木民俗文化形式和川人一起面对惨痛的现实,体现出乌木文化生命的坚忍品格。
乌木文化现实期特征。乌木文化现实期主要以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为特征。乌木行业规模主要以四川数百家从事乌木行业的成员为代表,他们从乌木作坊到乌木企业;从乌木作品陈列室到乌木博物馆;从乌木民间经济到乌木文化产业;从乌木文化艺术的研究到交流应用;从国内外乌木作品的收藏到社会团体,政府和中央省市领导的重视;从成都媒体到中央媒体、海外媒体的报道,构成当代乌木文化的发展形势。从新中国改革开放时间1980年至今,近30年的时间,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,大量的地下乌木被发掘出来,以厚重的历史文化素材,被四川民间收藏,伴随祖国与日俱增的繁荣兴旺,以清新的神秘文化状态,宣告乌木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淀,在新的盛世环境中被激发出新的活力。
乌木美誉主要以东方神木、东方文化的最高代表、环保世界的导师、和谐中国的鼻祖、太阳神鸟的栖所、万根同心太阳神、巴蜀第一奇、天府瑰宝、成都是乌木的家乡等为代表,她们共同旨向乌木厚重、悠远的神奇文化,饱含天府之国的秘史,和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激情,令世人格外激动。乌木美誉产生于庞大的乌木行业规模,这一物质基础所构建的人文环境,以及对乌木文化的深刻认识,其语义的内涵蕴藏了现实社会规律与历史社会规律之间,共同的乌木思想之宏观机制,以当代中国特色文明的雏形,展现国人未曾认识的乌木文明。
“乌木文物”一词的提法,基于乌木文化通过物质载体,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被传承下来的事实,其客观性等同于国家文物概念的定义,而考古学没有乌木课题,于是,没有乌木文物的说法和鉴定。但实际上乌木文物已经被国家作为文物认可,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,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,商业街出土的船棺,汉代的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等,这些文物都是标准的乌木文物。确定乌木文物这一名称,有力于乌木文物这个特殊的学术课题的成立,对研究和阐述乌木文化,乌木思想同中国文化之间,更广泛、更深入的联系,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2005年,太阳神鸟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家的认可,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,被正式使用,说明乌木文物,对当代中国认识中华文化史,处于领先地位。乌木文物仅为乌木文化的构件,所取得的当代成就,预示着乌木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建设,具有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。
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等构成的当代乌木文化现象,不是孤立的时尚文化,而是同中华文化历史有着脉承关系的,同中国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,极富历史喜剧性的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现象。
通观乌木文化历史期和现实期的地理关系,成都,现在的四川省会,同乌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神奇联系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,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,成都商业街船棺群,成都出土的汉代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乌木文物出现在成都区域,当今乌木文化现象起始于成都,并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规模,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所在地,学术界也基本认同在成都。把历史连接起来,从乌木神话时代起,至到今天六千余年的时间,足以证明,成都的确是乌木的家乡;乌木,的确是中华历史为成都、为中国注定的文化品牌。
从成都回望历史,那个主生众鸟的三白乌,她的家乡又在那里呢,是昆仑?还是成都?但可以肯定,很遥远的,创造乌木文明,魂牵中华民族的乌木王国就在成都。太阳神鸟为成都举起了乌木文化的旗帜,研究,发展乌木文化,就是研究,发展成都文明和中华文明。
乌木文化的神秘,不仅仅因为它源于中华民族创世文明的神话时代,乌木物质形成的巴蜀生态人文环境,乌木模式的奇异现象。并且,在历史的长河中,以成都为栖所,标注了中华文明秘藏乌木文明的线索。中华民族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,因为乌木文化的凸起,对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、成都平原众多的古代城址的认识,将会更加清晰一些;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将会进一步加强……成都将成为揭开许多谜团的焦点,必将引发考古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的新一轮重视。
通观乌木思想的实践历史,可以说: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乌木文化模式从乌木神话时代至到今天,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,其情志色彩或高昂、或喜庆、或悲沉、或低调,都伴生着相应的人文环境,符合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客观评价。
乌木神话时代,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所表达的天下大众迎光明的大气概,带着高昂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创世文明的雄心壮志。
汉朝时期的摇钱树、金乌画像砖,所表达的华夏太平、国富民强,带着喜庆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盛世社会的灿烂辉煌。
当代乌木文化现象的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所表达的大众安康、百业兴旺、国家强盛,带着欣荣的人文情态,伴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气象。
商殷时期的青铜神树,所表达的政治主张的异象,带着沉稳忧患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战争无情、摧残大众的时代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船棺文化,所表达的忧痛宿愿,带着悲沉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诸侯争霸、列国争雄的乱世局面。
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的兴起之后,乌木民俗文化带着低调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道、儒、佛文化的兴衰更替,一直走到今天。
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,产生的根因在于乌木模式的传承,与乌木思想宏观机制的相互依赖,乌木文化模式的形象逻辑,有利于乌木思想的形象实践,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形象思维特点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两者在乌木神话时代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社会功能定位,成为后世社会无法超越的主导者。乌木思想成为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“内因”,乌木文化模式则是“内因”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人文学说,但在“大众共存”这个根本思想的基础上,去实现大众获取象太阳一样光明,象鸟一样自由的生活,并同天地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立世学说,我们看到的唯有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。然而,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所遵循的立世原则,仍然是乌木思想。中国文化六千多年的历史,即是乌木思想的实践史,同是乌木文化的发展史。显然,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具有“大众共存,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实践真理性,在中国历史社会中,为大众共存万法实践之宗源。
由上,假若没有乌木文化,就不会产生乌木神话时代和乌木模式,亦就没有乌木思想,同样不会产生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,以及道、儒、佛文化两千多年的历史,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我们无法想象,从这个意义上断言: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
乌木文化,一则谓,以乌木神话时代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为本源,贯通华夏民族史上,通过乌木物态模式现象,得以反映的历史人文环境,以及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环境。二则谓,以乌木神话时代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,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的乌木思想,主导中华文化的进程,成为中华历史社会大众共存万法实践之宗源。
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人文环境,主要是第四纪晚冰期消融这一特大的主题事件,注入巴蜀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,形成以洪流为历史破坏性指标的生态进程中,巴蜀文化的演进无法避齐,“洪灾”这一生态背景的约束,和“天府之国”优越生态环境的吸引,产生认识自然,利用自然的因势利导思想,构成巴蜀先民以成都平原作为天堂的,特有的生态人文气质。乌木物质作为巴蜀生态背景的产物,其形成实况,对巴蜀先民当时的人文思考,和作为历史灾难记忆的传承,在更早期的乌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,共同合成的人文乌木,又构成巴蜀生态文化中特有的乌木人文气质。乌木人文成为生态人文的具体表现,以乌木物质和乌木模式作载体,代代传颂至今,这就是川人俗称乌木的来源。由此乌木物质形成的生态人文环境,是乌木文化不可分割的版块。
乌木模式的存在状态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用了“乌”和“木”两种基本的物态技术为特征,体现乌木思想发挥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客观现象。
为了明确乌木模式和乌木思想,所处历史环境阶段中的特征,对其历史时期进行划分,夏朝之前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;夏朝至汉朝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;汉朝至鸦片战争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;鸦片战争至1980年,谓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;1980年至今,谓乌木文化现实期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,主要以乌木神话为特征,乌木神话分别以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等乌文化和木(树)文化为代表,构成华夏民族创世文明的乌木神话时代。
史载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主生众鸟,亦为驮载太阳的神鸟,从黑暗中给大地带来光明;建木,立于天地之中,为众神上下天地的天梯;扶木、若木,一东一西,为乌之栖所。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等神话,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史前史,作为旧世界文化的终结,亦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,开启了创造新世界文明时代的历程。
“三白乌、三足乌”为标志的乌文化,以“三”代称“天、地、人”的概念;以“乌”代称“黑暗、光明和自由”的概念,在史前史,天、地、人共存的环境中,效法太阳(光明)、鸟(自由)、黑暗(阻碍大众获取光明和自由的一切天灾人祸)等自然物哲理之间的形象辩证,经过漫长时期的实践,总结出大众活动的宗旨在于“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。
“建木、扶木、若木”为标志的木文化,在对树崇拜的基础上,仍然凭借自然哲理的形象辩证,以木表达大众对光明的需要,就象树对太阳的需要一样,唯有光明的生活,大众才能象树一样自由成长。以扶木、若木表达大众生存的地理环境,在以建木为中心,从西到东的地域。以建木表达大众需要建设,保护大众生存及其环境的领导中心,经过长期的实践过程,总结出大众活动的根本思想在于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”。
以东扶木,西若木,为乌之栖所,表达乌文化和木文化的互动结果,产生了乌木文化;同时表达了建木所在地,是乌木文化的发展中心,一个实际存在的乌木王国诞生了。乌木文化以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,冲破黑暗,获取光明和自由”的乌木思想,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先河,标志着大众历史从人文启蒙主义的世界,走进了人文生态主义的世界。
大禹建立夏王朝的成功,可谓乌木文化在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开篇巨作。尧、舜、禹所处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天灾是洪水,最具代表性的人祸是十日争霸,即流传于后世的十日神话。十日神话内容甚多,如史书载:尧射十日、羿射九日、帝俊生十日、十日浴汤谷、十日栖息于扶桑与若木、十日齐现天空等等。十日神话之日,义同三足乌,为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领袖;十日之十,为多数。十日,为产生很多追求光明和自由的领袖,即为乌木文化的社会具体现象。因十日出现天空,万物焦枯,产生“尧射十日”(羿射九日乃夏王朝建立之后事),即“十日争霸”的社会尖锐矛盾。“尧之时,十日出,万物焦枯,尧上射十日,九日去,一日常出”。尧之时,十日争霸的社会矛盾得到解决,大众奉行乌木文化的思想得到弘扬,显示乌木文化发挥了强大的领袖力量。
今四川地区发掘规模的乌木实物,佐证了史书记载尧、舜、禹时代天灾洪水的真实性。在禹的领导下,天灾洪水及其伴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,随之而新生的夏王朝,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,结束了华夏民族一盘散沙的历史。在尧、舜、推崇乌木文化日渐光明的基础上,大禹王集团以民为本,把“乌木王国”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的理想变成了现实,以国家文明里程牌的创举,开发出一片乌木文化的新天地。
把一个大众生存的恶劣环境,变成了一个大众共存的良好环境,揭示出大禹王集团对待“天灾人祸”的生存环境,已经拥有了系统的环保思想和措施,其目的实现了乌木思想的要求,说明大禹王集团环保思想,是乌木思想之环保哲理内涵的具体表现。大禹王堪为中国文明史上的“环保大英雄”。
尧、舜、禹是中国历史上,乌木思想产生的社会主流文化现象。大禹王的成功,是乌木思想的成功,标志着一个具有社会管理能力,爱护大众共存环境的乌木文化集团已经诞生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二期主要以乌木历史事件为特征。乌木历史事件主要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,和成都市商业街发掘的船棺群为代表的船棺文化,他们以乌木模式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,这些事件具有浓厚神奇的乌木文化氛围。
青铜神树(同时出生的还有几棵残断的青铜神树)诞生在商殷时期的武丁时代,它承载了两组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鸟、三枝、三层、火轮、树”等构件的乌木文化信息,一组以“悬龙、刀、剑”为构件的龙文化信息,构件各执于树干之周围,组合成视觉冲击强烈,文化信息深厚博大,情志色彩沉稳忧患的青铜作品。无疑,青铜神树信息记载了乌木文化历史第一期的历史意义,标志着乌木文化的传承持续到了青铜神树诞生的时代。
“龙”是以黄帝为系统的北方文化集团的图腾,“刀、剑”是战争的象征。武丁时代,武丁发动了同历史相比,规模巨大的战争,“悬龙生刀剑”的信息;即是对武丁时代战争的真实记录。青铜神树两组信息都有独立的历史背景,表达了乌木文化集团与龙文化集团之间,治理社会不同的政治主张。乌木文化集团对龙文化集团采用战争手段进行了坚决的反对。由此,说明乌木思想在夏朝和商朝武丁之间的历史时期,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行为主导作用。青铜神树作为武丁时期乌木文化艺术的时代杰作,亦作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丰碑,透示出乌木思想在当时社会艺术领域中的核心地位。
从商朝到西周,乌木神话还在继续,玄鸟生商,巨鸟救后稷,意在传说商朝和西周都是三白乌的后代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夏、商、西周的兴盛衰亡都跟“大众共存、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乌木思想存在直接关系,王者爱民则国兴;王者欺民,则国衰;王者弃民,则国亡。
船棺文化出现在春秋时代初期,至汉朝初期,共五百余年的时间,主要活动范围在巴蜀地区,是乌木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重要代表。船棺文化对中国后世殡葬文化的影响巨大,黑(乌)色船型棺具,是船棺形式的发展,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至今,即为一大例证。船棺文化的本质是:春秋战国时代,出现诸侯争霸,列国争雄,诸子百家文化茂生的悲世局面。中国大地悲患四起,乌木文化集团的理想和抱负失去了生存环境,那些热爱大众共存,愤恨时代凄凉的子民们,在极端痛苦的命运挣扎中,孕育了“生不得志,死而宿愿”的信仰,创造了以乌木神话时代为精神导师,以先民的遗志为召唤,以行走天下的船木为葬棺,安置灵魂的殡葬文化,成为世界殡葬史上的奇观。船棺文化体现了乌木思想,在历史环境大变动的悲惨状态下,对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所起到的主导作用,有力地证实了乌木文化群体信仰,在群体灵魂祭拜大众光明文化的山峰上,为中华民族树造了一座乌木灵魂之塔。
春秋战国时代,是中国历史走到“大众共存”最为艰难的时期,它严重违背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与“乌木王国”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,没有夏、商、西周以民为德,中央集权的光明大器。以东周的建立为转折点,乌木思想急剧衰退,一直到汉朝,诸子百家文化无首——这是一个人祸黑暗压倒光明的时代,船棺文化尤如乌木的灵魂,在被魔鬼吞食的搏斗中留下的一点灵光,却明亮的可以穿透历史,照耀未来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主要以乌木文化艺术为特征。乌木文化艺术主要以成都出土的汉代文物摇钱树,和金乌画像砖为代表,他们散发的洋洋喜气,尽致地表达了盛世汉朝的辉煌成就,摇钱树运用树模式的艺术形象,同历史上青铜神树、船棺文化托载各个时代的重要社会事件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;翔天飞舞的金乌画像砖,同十日神话、玄鸟生商、巨鸟救后稷一样,源于乌木神话时代三白乌、三足乌。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,他们承担了同历史环境相应的使命,成就了不同环境的历史,共同选择的精神领袖。汉朝,以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管理的太平盛世,代替了一个结束诸侯争霸的混战历史,统一全国后,又迅速瓦解的秦朝,其乌木文化艺术的喜庆同船棺文化的悲沉相比,证实了汉朝在政治、军事、教育、道德、经济、艺术、民俗等多方面,主张“天下太平,百姓安宁”的大众共存世界,仍然应用了乌木文化的核心思想,并同先道后儒的文化模式一起,为汉朝的兴盛作出了贡献。退出历史舞台五百多年的乌木思想在汉朝得以复兴。
中国二千多年来,道儒佛为主流的文化格局,起始于汉朝。道儒佛文化都在宇宙、自然万物、国家、社会、人性、哲学、医学等多方面,各自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系统成就,却都运行在乌木思想的宏观世界里,以各自不同的本源主张学说,去实践乌木思想的旨趣,成为乌木思想宏观机理的受益者。
道文化以大道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自然法则,修无为,以道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儒文化以天、地、人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和谐辩证法则,修有为,以儒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佛文化以人心为本源,主张大众运用清净轮回法则,修无为,以佛家学说立世,建设乌木思想的世界。
乌木文化的出现,以创世文明的形态早于道、儒文化四千年以上的时间,都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统文化,都对中国历史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主导性。汉朝之前的道儒文化雏形已经产生,以禹、汤、文武、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“小康社会”,即是儒文化的雏形社会原态,又是道家文化的温床,同是乌木文化成功的典范。春秋时代集大成的道、儒文化领袖人物老子和孔子,为了解决现实矛盾,拯救天下大众的痛苦,鉴古证今
汉朝时期,以道、儒、佛文化作为乌木文化的新面貌,向纵深发展至今,标志着中华文化经历了,从人文启蒙主义到人文生态主义,再到人文形学主义的历史进程。
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特征。乌木文化历史第四期主要以乌木民俗文化为特征。乌木民俗文化主要以四川民间供奉乌木神灵,乌木神话故事流传,乌木饰品、乌木棺材、乌木家俱、乌木文房诸宝等为代表,它们保存了乌木神话时代的神秘性,并增加了娱乐性、收藏性、实用性功能,与乌木文化历史第三期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,盛兴之后的乌木民俗文化一样,同外界的交流范围大大缩小,偶有民间活动。乌木文化模式在社会政治、教育、文化艺术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复存在,表现为民间的散传形式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,作为中国与世界矛盾的分界点,中国文化从此与世界文化发生激烈碰撞,发展到全国性地多次卷入到矛盾的最高形式,第一次世界大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,在如此变幻莫测的时段里,中国道儒、佛等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。与此同时,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,战胜了外敌强权的侵略,和统一国内矛盾建立了新中国。马克思主义,毛泽东思想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则,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世界,同乌木思想是一致的,不同的是在具体的环境中采用了具体的方法。新中国的建立,完全可以看作是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,化解了更高级的社会矛盾,其哲理的宏观作用,是无以能比的。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,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代表的严重错误,又一次破坏了“爱护环境,大众共存”的社会行为准则,造成国家和大众的艰难局面,短短的140年的时间,中国社会遭受了巨大的人祸灾难,乌木文化没有中断,被天府之国传承下来,以乌木民俗文化形式和川人一起面对惨痛的现实,体现出乌木文化生命的坚忍品格。
乌木文化现实期特征。乌木文化现实期主要以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为特征。乌木行业规模主要以四川数百家从事乌木行业的成员为代表,他们从乌木作坊到乌木企业;从乌木作品陈列室到乌木博物馆;从乌木民间经济到乌木文化产业;从乌木文化艺术的研究到交流应用;从国内外乌木作品的收藏到社会团体,政府和中央省市领导的重视;从成都媒体到中央媒体、海外媒体的报道,构成当代乌木文化的发展形势。从新中国改革开放时间1980年至今,近30年的时间,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,大量的地下乌木被发掘出来,以厚重的历史文化素材,被四川民间收藏,伴随祖国与日俱增的繁荣兴旺,以清新的神秘文化状态,宣告乌木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沉淀,在新的盛世环境中被激发出新的活力。
乌木美誉主要以东方神木、东方文化的最高代表、环保世界的导师、和谐中国的鼻祖、太阳神鸟的栖所、万根同心太阳神、巴蜀第一奇、天府瑰宝、成都是乌木的家乡等为代表,她们共同旨向乌木厚重、悠远的神奇文化,饱含天府之国的秘史,和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激情,令世人格外激动。乌木美誉产生于庞大的乌木行业规模,这一物质基础所构建的人文环境,以及对乌木文化的深刻认识,其语义的内涵蕴藏了现实社会规律与历史社会规律之间,共同的乌木思想之宏观机制,以当代中国特色文明的雏形,展现国人未曾认识的乌木文明。
“乌木文物”一词的提法,基于乌木文化通过物质载体,历经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时间被传承下来的事实,其客观性等同于国家文物概念的定义,而考古学没有乌木课题,于是,没有乌木文物的说法和鉴定。但实际上乌木文物已经被国家作为文物认可,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,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,商业街出土的船棺,汉代的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等,这些文物都是标准的乌木文物。确定乌木文物这一名称,有力于乌木文物这个特殊的学术课题的成立,对研究和阐述乌木文化,乌木思想同中国文化之间,更广泛、更深入的联系,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2005年,太阳神鸟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家的认可,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,被正式使用,说明乌木文物,对当代中国认识中华文化史,处于领先地位。乌木文物仅为乌木文化的构件,所取得的当代成就,预示着乌木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建设,具有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。
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等构成的当代乌木文化现象,不是孤立的时尚文化,而是同中华文化历史有着脉承关系的,同中国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,极富历史喜剧性的当代中国特色文化现象。
通观乌木文化历史期和现实期的地理关系,成都,现在的四川省会,同乌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神奇联系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、三鸟环日图案、太阳轮、太阳符号器系列、鸟形器系列,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、鸟形器系列,成都商业街船棺群,成都出土的汉代摇钱树、金乌图像砖等乌木文物出现在成都区域,当今乌木文化现象起始于成都,并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规模,乌木神话时代的建木所在地,学术界也基本认同在成都。把历史连接起来,从乌木神话时代起,至到今天六千余年的时间,足以证明,成都的确是乌木的家乡;乌木,的确是中华历史为成都、为中国注定的文化品牌。
从成都回望历史,那个主生众鸟的三白乌,她的家乡又在那里呢,是昆仑?还是成都?但可以肯定,很遥远的,创造乌木文明,魂牵中华民族的乌木王国就在成都。太阳神鸟为成都举起了乌木文化的旗帜,研究,发展乌木文化,就是研究,发展成都文明和中华文明。
乌木文化的神秘,不仅仅因为它源于中华民族创世文明的神话时代,乌木物质形成的巴蜀生态人文环境,乌木模式的奇异现象。并且,在历史的长河中,以成都为栖所,标注了中华文明秘藏乌木文明的线索。中华民族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,因为乌木文化的凸起,对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、成都平原众多的古代城址的认识,将会更加清晰一些;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将会进一步加强……成都将成为揭开许多谜团的焦点,必将引发考古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的新一轮重视。
通观乌木思想的实践历史,可以说: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乌木文化模式从乌木神话时代至到今天,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,其情志色彩或高昂、或喜庆、或悲沉、或低调,都伴生着相应的人文环境,符合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客观评价。
乌木神话时代,三白乌、三足乌、建木、扶木、若木所表达的天下大众迎光明的大气概,带着高昂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创世文明的雄心壮志。
汉朝时期的摇钱树、金乌画像砖,所表达的华夏太平、国富民强,带着喜庆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盛世社会的灿烂辉煌。
当代乌木文化现象的乌木行业规模、乌木美誉、乌木文物所表达的大众安康、百业兴旺、国家强盛,带着欣荣的人文情态,伴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气象。
商殷时期的青铜神树,所表达的政治主张的异象,带着沉稳忧患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战争无情、摧残大众的时代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船棺文化,所表达的忧痛宿愿,带着悲沉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诸侯争霸、列国争雄的乱世局面。
自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的兴起之后,乌木民俗文化带着低调的人文情志,伴生着道、儒、佛文化的兴衰更替,一直走到今天。
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,产生的根因在于乌木模式的传承,与乌木思想宏观机制的相互依赖,乌木文化模式的形象逻辑,有利于乌木思想的形象实践,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形象思维特点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两者在乌木神话时代都已经完成了各自的社会功能定位,成为后世社会无法超越的主导者。乌木思想成为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“内因”,乌木文化模式则是“内因”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。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人文学说,但在“大众共存”这个根本思想的基础上,去实现大众获取象太阳一样光明,象鸟一样自由的生活,并同天地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立世学说,我们看到的唯有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。然而,道、儒、佛文化模式所遵循的立世原则,仍然是乌木思想。中国文化六千多年的历史,即是乌木思想的实践史,同是乌木文化的发展史。显然,乌木思想的宏观机理具有“大众共存,获取光明与自由”的实践真理性,在中国历史社会中,为大众共存万法实践之宗源。
由上,假若没有乌木文化,就不会产生乌木神话时代和乌木模式,亦就没有乌木思想,同样不会产生“乌木兴、中国兴,乌木衰、中国衰”的历史现象,以及道、儒、佛文化两千多年的历史,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我们无法想象,从这个意义上断言:乌木导演了中华文化。